槐花细碎的白瓣落在青砖缝里时,朋友正举着相机,对准南锣鼓巷的砖雕门楼。镜头的咔嗒声惊起檐角的麻雀,扑棱棱掠过垂花门,惊落一串铜铃的清响。我忽然发现,这些日日走过的胡同竟像从未相识的故人。
“这胡同里飘着槐花香呢。”朋友踮着脚,把镜头对准屋檐下的铜铃铛,她惊喜的语气让我赧然。我熟悉这里的每块砖石,知道哪户人家的门墩上趴着石狮子,哪扇雕花窗棂后藏着京剧的唱腔。可我从未驻足看过春深时青苔怎样沿着石阶慢慢攀爬,秋暮里斜阳如何将银杏叶染成半透明的金箔,在风中轻轻摇曳。那些年我总在朋友圈里艳羡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,却不知自家窗下就铺着层层叠叠的紫色泡桐花,花瓣落在自行车筐里,静谧而深情,宛如一封未寄出的情书。
记忆突然漫回年少时节。那时读王维的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总想着要去名山大川登高望远,仿佛唯有险峻的峰峦、云海间的道观,才配得上诗里的苍茫意境。那年重阳,父亲带我爬上小区后的小土坡,坡顶杂树丛生,野菊花在风里轻轻摇晃,发出细微的簌簌声。当我气喘吁吁爬上坡顶,望见整个城市在暮色中次第亮起灯火,楼群化作璀璨星河,远处长安街的车流像流淌的金线,霓虹与晚霞在天际线交织成瑰丽的绸缎。父亲轻轻揽住我的肩,说:“你看,风景不在远处,而在登高望远的眼睛里。”
前年春天去杭州访友,朋友特意带我去看太子湾的晚樱。粉白花瓣落在青石板上,像下着温柔的雪,沾在游人的发梢、肩头,也落在西湖的碧波上,随波荡漾。那飘落的花瓣,像是春天寄给人间的信笺。我想起北京法源寺的丁香,往年我总是行色匆匆,从那片紫雾中掠过,忽略了花影里隐约的诵经声,还有落在经书上的花瓣。朋友指着苏堤垂柳,说羡慕北国风光,我望着西湖烟雨想起什刹海的冰场——原来我们都在彼此错位的乡愁里寻找慰藉,总以为别处的风景才是最美的,却不知自己的生活也正被他人向往。
去年深秋,陪苏州来的阿姨逛故宫。她站在太和殿前,仰头数着檐角蹲兽,手指轻轻摩挲着汉白玉栏杆,忽然红了眼眶:“小时候听评弹里唱‘金銮殿上琉璃瓦’,今天才摸着这些冰凉的瓦当。”她的声音微微颤抖,带着岁月沉淀的感慨。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,夕阳正把红墙黄瓦镀成琥珀色,飞檐勾勒的天空蓝得让人心颤。这些我看了二十多年的景象,此刻竟陌生得恍如初见。阳光透过雕花窗棂,在金砖地面投下几何图案,光影交错间,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长廊。
前些日子整理旧物,翻出早年写满远方地名的笔记本。巴厘岛、塞纳河、乞力马扎罗的雪,字迹被岁月洇得模糊。夹页里掉出一张泛黄的北海公园门票,背面潦草记着:“今日和白塔合影,划船时遇见彩虹。”那歪歪扭扭的字迹,记录着曾经的快乐与惊喜。忽然惊觉生命中最清澈的光影,原来都藏在自以为庸常的褶皱里。
朋友离京那日,我们站在鼓楼大街看鸽群掠过灰瓦屋顶。鸽哨声在胡同上空回荡,悠长而空灵。民俗学家王世襄所说,天空中鸽哨的声音深入于人们生活之中,已成为北京的一个象征。那声音是老北京的记忆,也是城市的脉搏。朋友忽然说:“你知道吗?我老家门前的油菜花田,要坐三小时飞机才能让你看见它的美。”
我们相视而笑,想起米兰・昆德拉那句“生活在别处”,原来每个人都活成了彼此的远方。那些我们向往的远方,也承载着别人的乡愁;而我们习以为常的地方,在他人眼中,也是令人向往的风景。
暮春的晚风裹着槐香穿堂而过,什刹海的游船正点亮串串灯笼,在水面投下暖黄的光晕,像是撒落人间的点点星光。我站在四合院的玉兰树下,看树影婆娑,忽然懂得风景从来不在经纬度标记的远方,而在重新凝视的瞬间——当我们收起丈量山河的尺规,光便会从熟视无睹的裂缝里渗出来。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,那些藏在街角巷尾的美好,只要用心去发现,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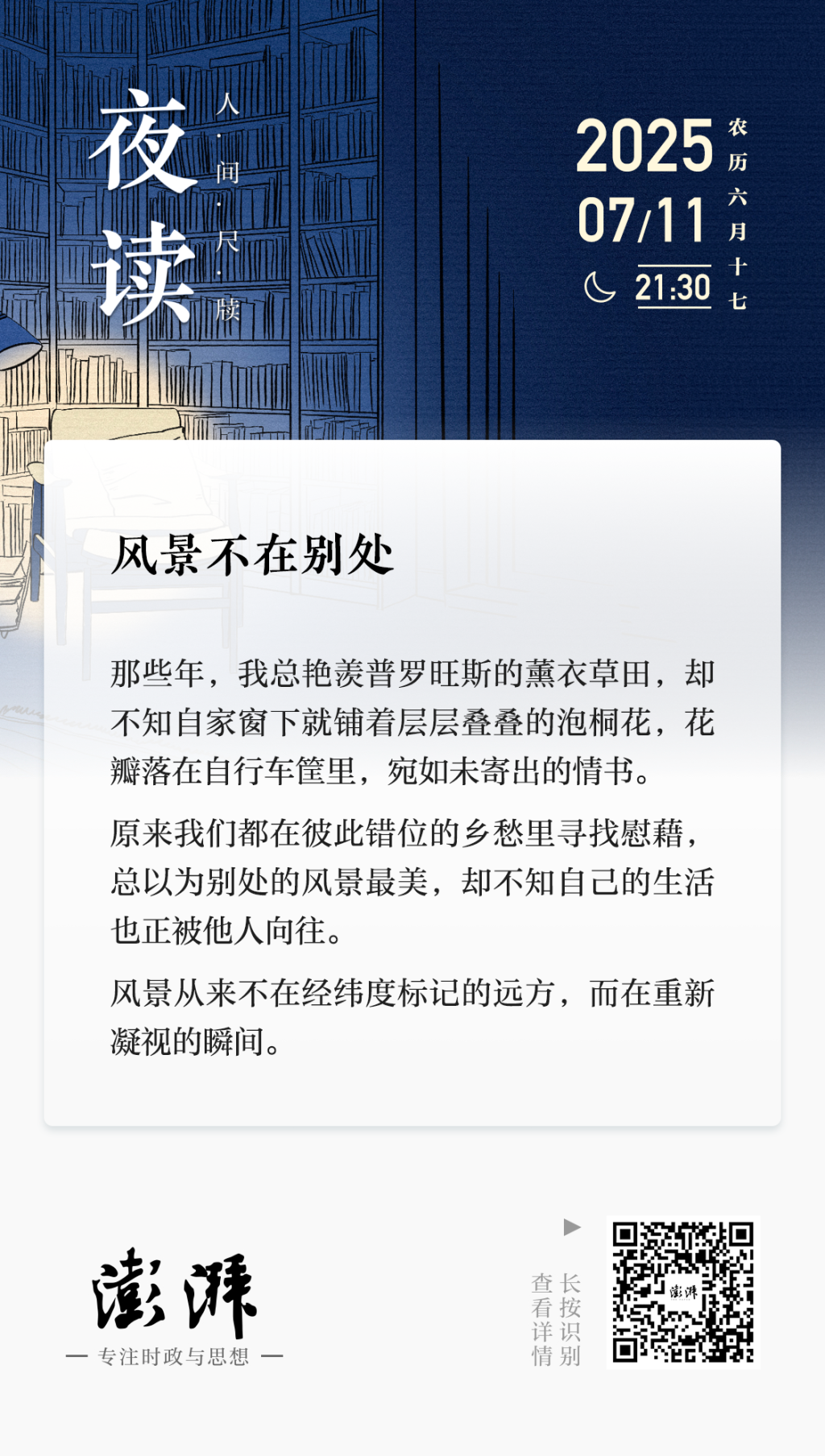


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